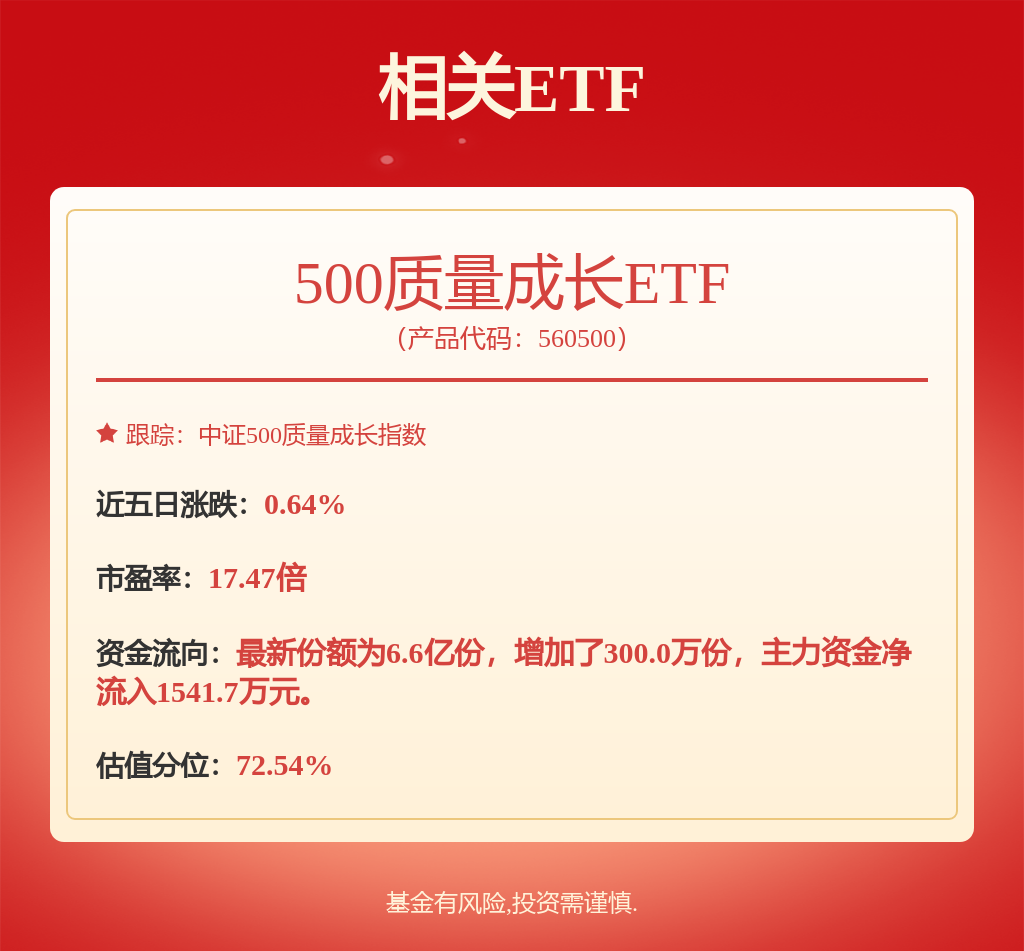摘 要 生育行为是人口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作为生育逻辑前端的生育意愿直接影响生育行为。从理论上分析互联网使用是如何通过影响生育条件、生育效用和生育信息影响生育意愿的,并基于CGSS2021的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论证。研究发现:
(1)总体上,互联网使用会对个体生育意愿产生负面效应,生育条件、生育效用在这种负面效应中起到中介作用,生育信息产生正面的调节效应。

(2)生育效用的中介效应存在性别差异,总体上生育效用对女性的影响更大,而男性较女性而言更重视生育的预期效用,女性则更看重生育的情感影响。
(3)良好的外部生育环境能缓解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提升社会流动性、营造和谐的生育环境有助于提升个体生育意愿。
关键词:互联网使用;生育意愿;生育效用;生育决策
作者简介:
吴本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樊庭君: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肖时花:《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一、引言
生育行为是人口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础。生育意愿作为人们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及看法,对个体生育行为和总体生育率有着重要影响[1]。伴随社会经济发展,中国社会老龄化、人口红利降低等问题愈发凸显,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极大地影响了个体的生育意愿,使得生育率降低[2]。2021年,中国进一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全面三孩”政策。然而,政策环境的放松并没有使人口走势向上,反而呈现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的态势。低生育率暴露出居民的低生育意愿,我国宏观人口政策的调整对居民生育率的影响力正逐步减弱。生育意愿作为个体在生育性别、理想生育数量、育龄选择方面的追求映现[3],主要受到生育条件、生育效用、生育信息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具体而言,生育条件包括收入水平[4]、婚姻状态[5]、抚养能力等,生育效用包括预期效用与现期效用两个方面[6],外部环境包括政策约束、社会舆论、经济发展等[7]。其中,生育条件与生育效用直接影响生育子女的成本与收益,直接影响个体生育意愿,而生育信息及外部环境则是对生育意愿的外部影响,通过影响人们的所处环境与思想观念,对生育决策过程产生间接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正深刻影响着经济与社会发展。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个体传统的学习方式、价值导向、消费渠道、工作岗位[8],也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对个体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广泛影响。理论上,一方面,互联网使用拓宽了个体的就业渠道,尤其提升了女性就业率,增加了个体收入[9],进而增强了生育意愿;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拓宽了居民的娱乐渠道,在丰富居民娱乐享受的同时挤占其闲暇时间,经由替代效应影响居民在娱乐与家庭中的时间配置,对个体生育决策产生影响,最终使个体生育意愿降低。此外,互联网使用降低了个体获取信息的成本,居民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到各种信息[10]。但互联网上的大量信息是未经处理的,无法保证其真实性,个体大量接受这些信息会对其生育意愿造成影响。
已有研究多是从家庭视角分析生育意愿,而对于生育意愿的研究随着我国网络普及与人口形势变化呈现出新形势。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愈发突出,值得深入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将研究视角聚焦个体生育决策,基于生育条件、生育效用及生育信息三方面分析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路径,分析使用互联网在经济层面与思想层面上对个体生育意愿形成的约束。同时,针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分析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及阶层流动中人们使用互联网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差异,对于扭转我国近年来逐步下滑的人口出生率具有政策性意义,对新时期人口增长理论研究也具有学术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生育意愿是个体在权衡生育行为的可获得收益与需要付出的成本后所形成的生育决策倾向。在经济层面上,生育子女这一行为要求个体的收入足以支付其生育子女所产生的成本,且生育带来的效用能支持其愿意做出这一决策。生育条件和生育效用反映了生育行为所产生的成本与收益,对生育意愿形成经济层面的约束。在思想层面上,人们需要获得足够的生育信息以支持生育行为,或是来自父母辈的直接经验,或是来自互联网或书籍的间接经验。不同渠道的生育信息影响了个体的生育判断,在思想观念上对个体的生育意愿产生约束。而互联网的使用对个体的生育条件、生育效用与生育信息都产生了影响,下面将围绕这三个方面就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做出分析。
(一)互联网使用与生育条件
基于生育意愿的经济层面分析,子女可以视作父母产出的产品,兼具消费品[11]与投资品[12]的属性。个体决定是否生育的关键在于,在收入水平的约束下个体权衡生育成本与生活成本能否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即生育子女所带来的效用是否大于为其付出的成本,因此生育条件表现为个体的收入约束与生育支出。
互联网使用会对个体生育条件产生影响。一方面,互联网使用能显著提升个体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的提升对生育意愿有着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会提升个体的物质渴求,促进其消费欲望。强烈的消费欲望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13],并提升女抚养成本,因而对生育意愿产生负向影响[14]。在消费倾向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在技术层面实现了更高效的娱乐方式,手机游戏、社交软件等基于互联网而诞生的新娱乐途径为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使个人效用获得巨大提升。但是,这种由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高效娱乐方式也会造成使用者的依赖性乃至成瘾性[15]。在替代效应影响下,比起可能会引致自身效用降低的生育行为,人们更青睐于将自己的收入投入互联网娱乐中,增加享乐消费支出。这将使用于生育子女的资金减少,导致生育意愿降低。于是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使用互联网对个体的生育意愿有负面影响。
假说1a:个体使用互联网经由影响生育条件对生育意愿产生负面影响。
(二)互联网使用与生育效用
生育效用反映了生育子女为个体带来的收益,分为预期效用与现期效用两部分。其中,预期效用是抚养子代成长后的未来收益,主要表现为养老效用与经济效用。而现期效用更多体现为享乐效用。中国有着传宗接代和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父母会催促子女生育,致使个体产生焦虑,而生儿育女有利于满足父母期望,促进家庭和谐,且子女的诞生本身能带给个体满足感,这是现期的消费行为,当生育子女的那刻甚至计划生育的那刻就能使个体获得效用。
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效用的影响也将分为预期效用与现期效用两个方面[16]。在预期效用方面,互联网使用直接影响个体的养老责任,赡养老人的义务影响个体是否生育[17]。养老动机是生育子女的重要原因之一,生育子女可以视作一种养老资源,因此子代的养老责任认知影响其生育决策。互联网使用使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政府养老,显著降低了子女养老的意愿[18]。养老责任的降低代表着养儿防老这一观念的衰弱,生育子女作为养老资源的重要性下降,养老效用的降低导致个体生育意愿降低。在经济效用上,子女成年后通过工作会获得收入反哺家庭,父母由此获得的效用即经济效用,子女可以视作父母的投资产品,父母效用会随子女效用增加而增长,传统社会中生育子女一直作为个体改善自身收入状况、提升社会阶级的重要手段。互联网的使用拓宽了个体投资渠道,将子女作为投资品的重要性下降;且互联网使用对个体收入有促进作用,随着个体收入水平的上升,生育预期的经济效用下降,最终导致个体生育意愿降低。
在现期效用方面,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的时间分配。互联网高效用娱乐方式的冲击会使个体产生沉迷网络娱乐的倾向,从而对个体分配给养育子女的时间产生挤出效应。相较于投入烦琐的育儿事务中,使用互联网进行娱乐为个体带来的效用更高,从而使个体产生远离家庭的倾向,削弱生育行为所能带来的家庭幸福感。同时,互联网使用促使个体的家庭观念发生转变。互联网加速了各种信息的传播,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念受到冲击,生育子女的道德约束降低,生育子女为个体带来的满足感下降,导致现期效用下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个体使用互联网会影响生育效用,从而对生育意愿产生作用。
在中国的家庭关系中,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传统,女性通常被认为更应该顾家,因此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往往扮演着家庭关系的维系者这一角色。而男性在社会认知中通常被告知要以事业为重,这对男性产生了远离家庭的推力。在这种基于性别差异形成的家庭定位下,夫妻对于生育效用的认知存在差异,女性往往更看重现期效用,而男性更重视在经济层面上保证家庭生活条件,更看重预期效用。
假说2a:生育效用的中介效应存在性别差异,对于女性而言现期效用的影响更强,而对于男性而言预期效用的影响更强。
(三)互联网使用与生育信息
个体进行生育决策的过程需要生育信息提供支持,生育信息涵盖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因此生育信息能通过影响个体对于社会、家庭及自我的认知,加剧或缓解个体的生育焦虑,影响个体对于生育行为的决策过程,进而影响生育意愿,对生育意愿形成思想层面的约束。互联网有着更低的信息获取成本,能高效满足个体搜索生育信息的需要[19]。在个人层面,随着互联网功能逐步完善,居民可以轻松地在互联网上检索生育相关知识,利用网络购物平台购买相关商品,这有效降低了个体生育的时间成本,能更好地辅助人们的生育行为,缓解生育压力。但个体使用互联网的同时社交观念发生变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大数据推荐算法愈加完善,大量可能会使信息浏览者感到不快的信息被过滤,仅留下个体所偏好的信息,形成信息茧房和回音壁效应[20]。久而久之,个体沉迷于互联网娱乐,对与人交往产生排斥感,使得生育意愿降低[6]。在家庭层面,网络信息媒体的发展使得更为平等的家庭观念和性别观念得到广泛传播,这有利于和谐家庭关系的形成,对生育意愿形成正面影响[2]。在社会层面,网络上自媒体蓬勃发展,各种社会事件大量传播,在大数据推送影响下,个体使用互联网会接触到大量社会新闻,从而增强其社会参与意愿,增强社会信任感,缓解生育焦虑,提升生育意愿。本文就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互联网使用通过影响个体生育信息对其生育意愿产生积极影响。
(四)互联网使用与生育环境
生育环境是个体生育行为所需要的外部环境支持,宏观层面上主要主要包括政策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在中观层面上包括地区托育服务设施、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等方面,在微观上则主要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不同的生育环境中个体的生育压力存在差异,较好的生育环境能缓解个体的生育压力,进而促进其生育意愿。这之中个人发展与社会总体的发展环境高度相关,社会流动性的高低更是个体发展机遇的体现,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会给予个体社会阶层上升的期望,社会阶层上升意味着个体能掌握更多获取社会资源的渠道以期获得更多社会资源,从而营造出良好的生育环境,促进其生育意愿。在受到互联网使用所带来的生育负面影响时,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个体由于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能更加从容地进行生育决策,使得他们更难以陷入生育焦虑。此外,中国有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生育传统,这一观念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而在较高社会流动性的社会环境下,个体的子女更容易实现阶层上升,在这种生育环境中个体的生育意愿将会提升。本文就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4:较高的社会流动性能减少个体使用互联网对其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CGSS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内容涵盖居民网络使用情况、受教育水平、家庭关系与生育状况、健康状况等诸多研究主题,与本文的主要研究方向相契合。CGSS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满足本文研究需要。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育龄人群,故对总样本进行了筛选,删除了16~55岁育龄区间外的所有样本。此外,为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删除了样本中的空缺值以及其中的拒绝回答、不知道、不清楚等无效数据。清理筛选过后,最终得到3616个有效样本,男性样本1591个,占44%,女性样本2025个,占56%。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个体生育意愿,采用CGSS2021中“如果没有政策限制,您希望有几个孩子?”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指标。考虑到现实生育情景中极少有生育超过5个子女的情况,防止受到极端数值的影响,将理想子女数大于等于5个的变量进行合并。在去除空值后,由表1中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可见,生育意愿最大值为5,最小值为0,有效样本数为3616个,生育意愿平均值为1.81,可见大多数人的理想生育子女数为2个以下。
2.核心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个体互联网使用频率,采用“过去一年,您使用互联网的情况是?”这一问题的答案来测量,问题答案由低到高分别表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频繁”五个等级,赋值1~5。其中,有效样本数为3616个,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平均值为4,这表明绝大多数人保持较高的互联网使用频率,互联网的使用对个体生活造成了较深的影响。
3.中介变量
为了分析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引入个体生育效用及生育条件作为中介变量,选用“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应该由谁负责?”以及“你是否进行投资活动?”问题的答案作为生育子女的养老效用和经济效用的代理变量[17]。养老效用变量根据个体是否认同由子女承担养老主要责任的答案,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之所以选用该变量,是因为在中国家庭环境下,养老期望反映了个体对养老的态度,反映出其对子女养老的效用。样本主体越期望子女养老,则其生育的养老效用越高。经济效用变量为二值变量,该变量可以体现出个人的投资倾向。若个人存在其他投资渠道,则会对子女的经济效用产生挤出。而家庭期望变量选用问题“不管本人想不想生孩子,只要父母想要,我们就应该满足父母的意愿而生孩子?”的答案作为代理变量。通过受访者的回答能得出其对家庭构成的态度。样本越赞同这一观点,意味着其生育现期效用越高。
在生育条件方面,采用受访者年总收入对数作为收入水平的衡量变量,而消费倾向通过受访者的物质渴求水平进行衡量,变量构筑的具体做法是将受访者年总收入排序后平均划分为10个等级,然后用实际收入等级除以受访者的自评收入等级。物质渴求水平的高低代表了受访者的消费能力及其消费扩张倾向。
4.控制变量
个体在使用互联网时受到自身信息素养的影响。由于信息素养不同,个体对于网络信息的识别、筛选能力存在差异,因此信息素养在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影响中存在异质性。受数据限制,并没有能直接测度个体信息素养的变量,但个体的信息素养受到其学习能力的深度影响。个体学习能力越强,掌握的数字资源就越多,表现出越高的信息素养。因此,本文选取了“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这个问题的答案作为衡量标准。“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划分为0-2三个等级,0代表初中及以下学历,1代表高中及大专学历,2代表本科及以上学历。
本研究设置了个体禀赋层面、个体后天层面和经济层面三个层次的控制变量[6],其中年龄、健康状况、性别、民族为个体禀赋,宗教信仰、政治面貌、受教育水平为个人后天要素,住房、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收入水平为经济要素。
5.模型构建
本文研究内容分为四部分,即居民使用互联网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生育条件、效用的中介效应,生育信息的调节效应以及不同生育环境人群的异质性分析。由于本文中因变量为有序离散变量,故采用Ologit模型进行分析,基准模型具体形式如下所示:
方程中,因变量为代表个体j的生育意愿,本文采用CGSS2021问卷题目“在没有政策限制的条件下,你计划生育几个孩子”作为生育意愿的替代变量。生育意愿变量表现为计划生育儿女个数,所以统计上是离散非负的,i表示计划生育子女数的集合;核心解释变量为,代表了个体j的互联网使用频率;代表控制变量的集合,它是对控制变量的加总,涵盖了个体先天禀赋、个体后天禀赋和经济要素三个层次,包括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宗教信仰、政治面貌、收入、社会保障等要素。代表模型无法观测到的误差项。在Ologit模型中,自变量回归系数表示因变量和两个事件发生的相对比例。
本文的因变量为离散变量,且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为类别变量。为了检验中介变量的合理性,借鉴温忠麟[21]的类别变量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采用逐步回归法对中介变量进行验证,构建模型如下:
方程中,为中介变量,代表个体i的生育效用。首先用方程(1)对总效应进行检验,若系数显著则对方程(2)进行检验,若方程(2)中系数显著则代表中介变量与因变量相关,进而对方程(3)进行检验,当系数和同时显著时,则中介效应显著。此时,若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反之为部分中介。
为了检验异质性,本文引入了多个交叉项变量,因此可能导致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减少模型偏误,对多个交互项相关变量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然后使用去中心化后的交互项进行回归。这样便能使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得到控制。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验证基础模型的显著性,依照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列(1)中控制了个体先天禀赋的变量,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个体使用互联网的频率加深,会对其生育意愿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列(2)至列(3)逐步添加了控制变量,进一步控制个人后天禀赋和经济条件。在依次添加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趋向于稳定,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回归系数变动幅度减小,在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为负。本文中因变量为限制因变量,为了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列(4)和列(5)依照Tobit及OLS方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依然在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是稳健显著的,个体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越高其生育意愿就越低。
互联网已经实现了深度普及,使用互联网已融入个体的工作生活之中。虽然人们通过使用互联网能极大地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方便工作生活,有利于降低生活成本,高效规划时间进而增加空闲时间,对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但互联网的使用也会使个体消费扩张,增加生活成本。同时,人们容易沉浸于网络娱乐,挤占家庭时间。此外,网络上的负面信息会加剧生育焦虑,对生育意愿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假说1得证。
(二)内生性与稳健性分析
本文的内生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变量间的双向因果问题。已生育群体一般是年纪较大的群体,当其使用互联网检索生育相关信息时很有可能处于已经怀孕或者准备怀孕阶段,这导致了她们使用互联网的频率上升,而年龄的上升人的生育意愿会本能地下降,这就导致了有可能是因为已经生育导致了互联网使用频率的上升和生育意愿的下降,这是其中一种双向因果来源。二是变量遗漏问题。实际上,影响生育意愿的社会因素很多,无法将所有变量都纳入控制。个体的互联网使用便有可能跟其中的影响因素存在关联,进而产生内生性。为了消除内生性的影响,需要将互联网使用变量从个体中分离出来。因为个体容易与各种社会因素产生关联,本文构筑了省际互联网使用频率作为工具变量。省际互联网使用频率明显与个体的生育意愿不想关,因为这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对于微观的个体生育决策影响甚小,而省际互联网使用频率由个体互联网使用频率构成,两者间存在高度相关性,所以省际互联网使用频率可以作为个体生育意愿的工具变量。
参照Angrist & Krueger的研究[22],在模型设定正确的前提下,将因变量视为连续变量,用2sls进行回归的参数方向与显著性应该与Ologit模型一致,故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检验工具变量是否为弱工具变量,可以看到一阶段F值一直维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可以认为工具变量与自变量高度相关。其次,通过观察2阶段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省际互联网使用频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一致,且在添加了代表个人先天禀赋、后天禀赋、经济条件的控制变量后始终维持显著。由此可见,在控制了模型内生性后,互联网使用频率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回归结果仍然显著为负,可以认为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五、机制分析
(一)生育条件影响机制
互联网使用改变了个体的生育条件,对个体的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都产生了影响。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验证其在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生育意愿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列(3)显示个体使用互联网对其收入水平有着显著正向影响,收入水平的改善会改善个体的生育条件,但列(4)显示收入水平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这与当前的生育发展趋势相同。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普遍上升,绝对收入不再是个体生育条件的首要影响因素,生育的相对成本的重要性越发突显。列(1)显示个体使用互联网对物质渴求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物质渴求的增长意味着个体使用互联网存在消费扩张的倾向,直接导致个体用于生育的资金趋于紧张,对生育支出产生挤出效应,恶化个体的生育条件,列(4)的回归结果印证了这一点。物质渴求的中介效应显著,代表着互联网使用促进了个体的物质渴求上升,促进了个体消费扩张,最终在个体的生育决策中,由于生育成本的上升,最终导致生育意愿下降,假说1a得证。
(二)生育信息影响机制
生育信息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来自社会、家庭、个人三个方面,因此本文依据CGSS2021数据中对“社会是公平的?” “您是否赞成男主外,女主内?”及“您是否认为社会上的人是值得信任的”三个问题的回答分别构筑个体的社会观念、家庭观念以及社交观念三个方向的指标,回答取值1(非常不认同)-5(非常认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列(3)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在个人层面上,个体使用互联网获拓宽了其社会交往渠道,使得其对他人的信任感增加,促进了其生育意愿提高。在家庭层面,列(2)交互项回归系数同样为正,表明个体使用互联网促进了性别观念平等观念的传播,有利于和谐家庭关系的形成,使个体更愿意生育。在社会层面,列(1)报告的社会观念交互项的回归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促使个体对社会环境形成良好的认知,有利于其选择结婚、生育,对生育意愿起正向影响。综上所述,生育信息在个体、家庭、社会三个层面上促进了个体生育意愿的增长,缓解了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起到了正向的调节效应。假说3得证。
(三)生育效用影响机制
本文将中介变量生育效用分为养老效用、经济效用与享乐效用三组,按照模型(2)和模型(3),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检验。表6和表7报告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其中表6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对个体预期生育效用及现期效用都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个体使用互联网拓宽了投资渠道,经由替代效应降低了生育子女的经济效用。此外,互联网的使用还降低了个体的养老责任,使得个体选择子女养老的倾向降低,总体上期望效用降低。在现期效用方面,互联网使用的提升降低了个体对于传统生育观念的认同感,个体对子女效用的认同感降低,导致生育享乐效用下降。
表7报告了模型(3)中回归总效应的检验结果。列(2)结果显示,经济效用的中介效应显著为负,个体使用互联网拓宽了投资渠道,未来收入来源渠道多样化,对以子女未来收入作为预期收益的经济效用产生了替代效应,使得生育子女的经济效用降低,生育意愿下降。列(1)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个体的养老期望,由于生育子女的养老效用降低了,个体生育意愿下降。综上所述,互联网使用降低了个体的预期效用,对其生育意愿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于现期效用而言,列(1)结果显示,互联网的使用降低了个体的家庭生育期待,对生育的享乐效用产生了负面影响,享乐效用的降低对生育意愿形成负面影响。由此,假说2得到证明。
(四)异质性分析
效用是主观的感受,不同性别对生育效用的感受存在差异。为了准确分析生育效用的中介影响,需要分析生育效用的性别差异,本文依据性别分组重新按照模型(2)和模型(3)进行回归。模型(2)性别分组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结果显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使用互联网都降低了养老期望,并促进了其投资倾向,同时降低了个体的家庭期望,这与之前的总体回归结果相同。而对比两组回归结果发现,男性生育的预期效用影响比女性大。这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中男女的性别差异,男性更看重生育的利益影响,而女性则更看重生育的情感影响。
依照模型(3)进行中介效应性别分组检验的结果显示,女性的生育效用中介效应较男性而言更为显著,说明女性受到生育效用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中,女性更多承担了维系家庭的职责,经济职责多为男性负担,生育子女带来的收益对女性而言影响更大,所以女性的生育意愿受到生育效用的影响更深。此外,男性的经济效用中介效应并不显著,而女性显著,这同样印证了前文观点。女性此前较男性收入渠道少,其使用互联网获得了更多提升收入的渠道,导致女性生育子女带来的经济效用下降,最终使其生育意愿降低。
六、进一步分析
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的生育意愿产生整体的负面影响,但不同群体间影响的效果存在差异。本文针对阶层流动性差异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分别设置了互联网使用与个体主观阶层认知、主观阶层流动、客观代际阶层流动的交互项,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比较不同阶层群体使用互联网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主观阶层流动方面,本文依据受访者当年的阶层认知与其10年前的阶层认知的差值构筑了主观阶层流动性变量,其中阶层下降赋值为-1,阶层不变赋值为0,阶层上升则赋值为1。而在客观代际阶层流动方面,本文通过比较父代与子代的阶层差值构筑了代际流动变量,赋值与主观阶层流动相同。阶层认同变量则是个体当前自评社会阶层。将三个交互项分别纳入模型(1)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
列(1)显示主观阶层流动与互联网使用频率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互联网使用频率回归系数相反,这意味着个体由于阶层上升,生活地位改善,会更愿意做出生育子女的决策,且阶层的上升使得个体能为子女提供更良好的生活环境,网络上的生育焦虑内容对个体生育意愿的负面冲击能得到消解。列(2)中主观阶层认知与互联网使用频率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同样印证了个体阶层与生育意愿的正向关系,当个体处在更高的社会阶层,使用互联网对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更低。列(3)中代际阶层流动与互联网使用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是因为,阶层上升的群体往往具备了较高的个人资源禀赋,具备了更优秀的互联网使用及信息识别能力,其生育意愿难以受到使用互联网的冲击。综合来看,无论是主观或客观,随着个体阶层的上升,其生育意愿随之提升。阶层上升意味着生育环境、生育条件的改善,这将降低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
七、结论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3616个样本数据,文章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一,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的生育条件产生了负面影响,使用互联网虽能帮助个体收入水平上升,但同时也拉高了其物质渴求与消费支出,享乐消费的扩张会挤占生育支出,最终对生育意愿产生经济约束,抑制个体生育意愿。二,互联网拓宽了信息获取边界,使用互联网增进了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信任感,有利于平等家庭观念的形成,在生育信息层面对生育意愿产生正面影响。三,生育效用在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中起中介效应,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个体的生育预期效用,预期效用的降低导致其生育意愿下降。此外,男女间生育效用存在差异,女性群体更看重生育的情感影响,而男性更看重经济影响。四,社会阶层流动与个体生育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个体阶层上升将抑制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居民的生育意愿与社会发展和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对于内部的小家庭而言,家庭关系的不和谐是引起个人使用互联网逃避家庭责任,使生育意愿下降的诱因。因此和谐平等的家庭关系是提升个体生育意愿的关键,保护好婚内妇女权益,男性应与女方共同努力维系家庭稳定,婚内平等的家庭关系能增进生育效用,降低网络中负面生育舆论对生育意愿的干预。而在外部的社会大家庭中,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只有不断促进社会公平,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才能为个体提供良好的生育环境,充足的社会流动性会促进个体生育意愿提升。但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网络平台提供商为了提升流量、保证用户黏性,长期推送极端信息内容,助长了年轻群体的恐婚恐育现象。这需要社会与平台加强对信息内容的自主审核,保证育龄群体获取客观的生育信息,平台方要肩负起社会责任,维护网络舆论风气,引导正确生育舆论观念形成。
参考文献
[1]张霞,夏巧娟.生育意愿与生育率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8(12):108-120.
[2]吴帆.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否存在?——对后生育率转变国家(地区)生育率长期变化趋势的观察[J].社会科学文摘,2019(9):59-61.
[3]吴帆.生育意愿研究:理论与实证[J].社会学研究 ,2020(4):218-240.
[4]李子联.收入与生育:中国生育率变动的解释[J].经济学动态,2016(5):37-48.
[5]Zheng Z Z. Reproductive behaviour and determinants in a low-fertility era in China[J].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2019,15(2): 127-130.
[6]Becker G S,Barro R J. A reformul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8, 103(412): 1-25.
[7]王军,王广州.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研究及其政策意涵[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7(2):201-212+217.
[8]李飚,赖德胜,高曼.互联网使用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J].南方人口,2021,36(2):65-80.
[9]蒋琪,王标悦,张辉,岳爱.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影响——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劳动经济研究,2018,6(5):121-143.
[10]王小洁,聂文洁,刘鹏程.互联网使用与个体生育意愿——基于信息成本和家庭代际视角的分析[J].财经研究,2021,47(10):110-124.
[11]Becker G S, Lewis H G.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3,81(2):S279-S288.
[12]Boldrin M, Jones L E. Mortality, fertility, and saving in a Malthusian economy[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02,5(4): 775-814.
[13]Barber J S. Ideational influences on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attitudes toward childbearing and competing alternatives[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2001,64(2): 101–127.
[14]陈卫民,万佳乐,李超伟.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J].人口研究,2022,46(3):16-29.
[15]邱磊菊,冯宜强,史宇鹏,孙宝文.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J].人口研究,2022,46(3):3-15.
[16]李家聘,苟翠萍,谢冰,胡永国,吴宗辉.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路径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2,39(5):390-395.
[17]王晨.预期效用视角下家庭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D].湖北大学,2019.DOI:10.27130/d.cnki.ghubu.2019.000193.
[18]孟愈飞.中国居民养老模式选择的经济学分析[D].山东大学,2020.
[19]Hamza A, Sharma M K, Anand N, et al. Urban and rural pattern of Internet use among youth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mood state[J]. Journal of Family Medicine and Primary Care, 2019, 8(8): 2602-2606.
[20]Dettling L J. Broadband in the labor market: the impact of residential high-speed internet on married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J].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2017,70 (2):451–482.
[21]方杰,温忠麟,张敏强.类别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J].心理科学,2017,40(2):471-477.
[22]Angrist J D, Krueger A B.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fication: from supply and demand to natural experiment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1, 15(4): 69-85.(吴本健 樊庭君 肖时花)